
近年來,“新制造”這一概念成為市場熱詞,越來越多的企業和機構紛紛對其進行探討。但很多人在理解“新制造”時,往往會將它與技術、智能化等詞關聯起來,并認為這些東西對于傳統制造型企業來說遙不可及。
但是,作為一家傳統制造型企業的當家人,“雙童”樓仲平卻對此持有獨特的見解。那么,他到底是如何理解“新制造”的呢?快跟著吸管妞一起來看看吧!
“新制造”首先應該解決思維問題
“新制造”這一概念在被提出之后,出現了各種各樣的“別名”:智能制造、工業互聯網、工業4.0等等。這些名稱其實不過是不同國家不同時段對“新制造”的不同叫法,這個問題的背后,其實是“新制造”無法定論。既然如此,我們該如何理解它呢?
1962年,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托馬斯·庫恩在《科學革命的結構》一書中,首次提出“范式”概念。在此書中,“范式”指的是體系或范例,是在一個時代里人們公認的處理科學問題的前提,擁有系統的思想體系。
樓仲平認為,理解“新制造”,首先應該從思維上進行認知,因為這是“新制造”最核心最底層的東西。“新制造”本質上就是時代發展下一種范式轉換,從原有的工業化范式轉換為互聯網范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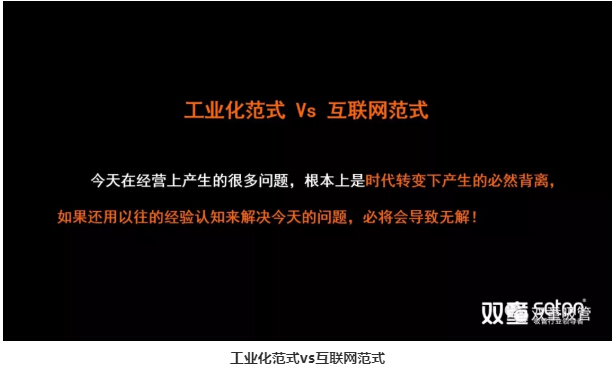
隨著范式的轉換,我們對制造業的認知和理解需要發生轉換,“新制造”首先應該是范式轉換下的一種新思維。唯有用新的思維,才能理解制造業在新時代下發生的變化。
下面,我們來理解一個概念——“要素拆解”。
要素拆解與擇優組合
什么是要素拆解呢?就是將一種事物按照一定的邏輯,層層拆解,拆成一個個單一要素。
舉個例子,比如一架波音飛機,我們可以把它拆解成:發動機、擾流板、方向舵、外部天線、座位…….而將這些部件繼續拆分,還可以拆解成合金、塑料、橡膠、玻璃等等,最后看到的是礦產和元素。
唯有通過對事物進行不斷的要素拆解,才能看到“更多的真相”,才能獲得更多事物之外常人難以看見的內在屬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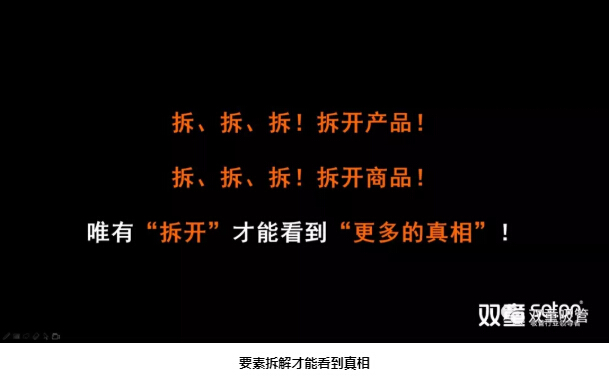
而要素拆解的最終目的,就是將拆解后獲得的這些屬性重新進行擇優組合,從而創造出全新的產品。
創新經濟學之父約瑟夫·熊彼特,曾在其著作《經濟發展理論》中對“創新”做了重新定義:所謂創新就是生產過程中的要素新組合,從而撬動顧客消費新需求而無關新技術。企業家要做的就是把現有的要素做重新的組合,創造出新的產品、技術和服務。其本質就是所謂的創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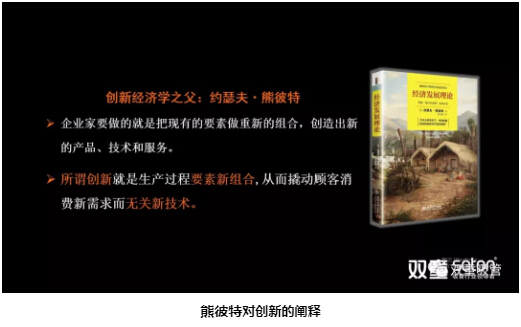
通過以上敘述,我們能夠明白,大多數的看起來高大上的創新,實際上都是要素拆解和擇優組合之后的結果。
有了以上的基礎認知之后,我們再結合案例來理解“新制造”:
“一根吸管”的“新制造”
在很多人的印象中,一說到“吸管”,就會習慣性的認為:吸管只值幾厘錢,不過是用來喝飲料的,沒必要做品牌、定標準……
實際上,這些都是大家在認知事物時所設定的一種隱含假設。所謂隱含假設,就是在你思考問題時,由于思維慣性或者過去的經歷、習慣,下意識采取的看待事物的方式,結果是掉入了這些思維陷阱,而看不到更多的可能性選項。
在隱含假設的限制下,我們很容易形成固定的思維認知,陷在舊范式里無法自拔。那么,我們要如何打破它呢?
以手機為例,最早的手機只能用來接打電話,但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,人們開始追問:手機真的只能用來接打電話嗎?不能用來拍照嗎?不能連接互聯網開發出更多功能嗎?
看看我們現在使用的手機,答案自然不言而喻。

我們再回到吸管的案例上,雙童”在二十多年前就打破了隱含假設,不斷進行內部追問和反思:吸管為什么一定是用來喝飲料?吸管為什么一定只能賣幾厘錢?吸管為什么一定要塑料材質?
2005年,“雙童”創造出了集聚娛樂性、功能性、創意性于一體的創新類吸管。
2006年,“雙童”研發出了以玉米淀粉為原料的PLA生物質可降解吸管。
2018年,“雙童”又推出了以天然淀粉為原料的可食用淀粉吸管。
…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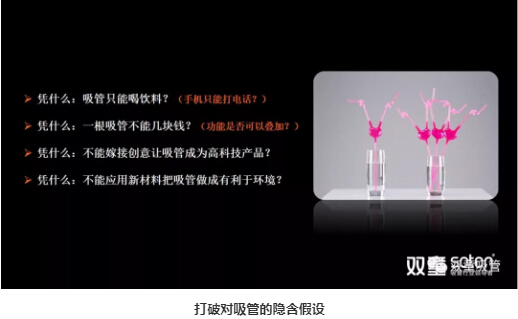
實際上從2005年開始,“雙童”就已經轉入到了“新制造”的范式當中,通過打破隱含假設,找到更為正確的基石假設,跳離傳統紅海,作出了符合現代科學的轉變。
接著,我們再來看看另外一個案例:
張一鳴的字節跳動公司,被稱為“APP工廠”,其APP的研發效率較高,用戶認可度也名列前茅。如旗下的“今日頭條”橫掃移動端圖文信息市場,“抖音”也成為短視頻領域的領跑者。其中的奧妙就是:這些新APP都是字節跳動將已經掌握的技術要素進行模塊化組合,從而快速批量開發出能獲得用戶認可的APP。
由此可見,不僅僅是傳統制造型企業能夠通過科學認知轉入“新制造”范式,互聯網行業、服務業等各種業態都可以通過轉變思維,組合創新等方式來實踐“新制造”。
因此,“新制造”并不局限于傳統制造業,只要能制造出新的、有效的、符合顧客需求的內容就都屬于“新制造”的范疇。
最后,吸管妞還是用馬云的話來作結:“新制造的班車已經開始啟動,不加速自己企業,不去擁抱未來的變化,不改革自己,我相信未來10-15年,大家都會哭天喊地。”
未來的變化是必然的,你的企業擁抱變化了嗎?